
周洁茹2015年香港西贡留影
内容摘要:70后小说家周洁茹于上世纪90年代声名鹊起,停笔十年的她重新回归小说创作,近年的短篇小说更是呈现纷繁的面相: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交叠出现,在地理空间意象、他者视角、女性经验的在场与权利话语的缺席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本文试从“香港故事”和“女性经验”的创作谱系出发,论述周洁茹近年短篇小说创作的叙事范式、审美内涵与思想价值。
关键词:周洁茹;小说;香港;女性;叙事
用“回归”来概括周洁茹和她的小说再恰切不过。1991年,中国的“新生代”女作家集体崭露头角的年代,1976年出生的周洁茹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1996至1998年,周洁茹的创作呈“井喷”状态,她发表的作品总计百余万字。对一个年轻写作者而言,如此成绩意味着,只要继续创作和发表,就能逐步奠定在文坛的“江湖地位”。然而周洁茹并没有循着这道轨迹走下去。1999年,成为专业作家的周洁茹开始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妖的网》。十几年后,“归来”的小说家周洁茹在《十年不创作谈》中警惕地自嘲:“很多时候,专业作家的位置会毁了一个作家,因为专业作家太幸福了,专业作家不用坐班,专业作家可以睡懒觉,专业作家被尊重,专业作家是行政编制……专业作家一百年没有新作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专业作家了。”这种“幸福感”令周洁茹感到了危机。2000年,24岁的周洁茹离开中国去了美国,这年是她生命的转折点和创作的分水岭。此后她的写作处在不稳定的状态,直到移居香港七年,才又重拾小说,清理此前动荡的人生。
2000年至今,周洁茹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花》《天涯》等刊物发表的小说,加起来不过二十篇;2013年以后刊发的小说占了总发表数的一半。这批作品大体分两类,一类是“香港故事”:以书写异乡人在香港的生活经验为主,计有《到香港去》《旺角》《邻居》(原名为《新界》)《尖东以东》等,它们基本以香港“地名”为题目。《邻居》尤其值得注意,小说原名《新界》(沿用“香港地名”的命名套路),其内在刻画和叙述的,仍旧是香港逼仄的公寓楼、人情、世态,聚焦的仍旧是活生生的香港经验;另一类小说,笔者称之为“女性故事”,计有《幸福》《生病》《结婚》《离婚》等,都与女性生命攸关,一起一落,大开大阖,写现代女性的生存体验与精神疼痛。笔者借助这两批小说来剖析周洁茹的创作范畴与叙事特征。
一.香港故事:地理空间与他者视角
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从《到香港去》,再到《邻居》《旺角》《尖东以东》——勾勒出陌生化视角下的香港。这批“香港小说”,有着与葛亮的“香港主题”小说集《浣熊》不同的韵味。葛亮以“新港人”身份,力图摘除其异乡人特征,用本土(对话中粤语的使用、对香港民间习俗的洞察等)的方式临摹尘世男女的香港故事;他的小说与刘以鬯、西西、也斯、黄碧云、董启章等香港本土作家一起构成鲜亮的风景线。倘若沿着这道轨迹将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也纳入此范畴,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流派划分显得生硬和牵强。在“新世纪香港小说趋势”研讨会上,周洁茹的发言袒露出其尴尬的“香港身份”:“所有除我之外的新来港人士,都是在第一个月就学会广东话了。因为要融入香港社会,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这样,时刻准备着,要离开香港。不会广东话,是我的遗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广东话的模式来写我的香港小说,让它们成为最香港的小说。”这里的广东话(粤语)与“最香港的小说”之间有着某种吊诡关系。她的“声明”和香港故事形成奇特对照。换言之,周洁茹没有使用粤语来写有关香港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她无法呈现真实或者是“另类”的香港。很明显,在周洁茹的语境中,“最香港”这一定语是需要被重新打量的。
什么是“香港小说”?是否故事发生在香港,就可以宣称自己归属这个概念?难道只有香港本土作家才能写出地道的“港味”小说吗?周洁茹的小说是对“香港小说”的反诘与逆写,是对“香港”这一主体意识的颠倒。周洁茹用其鲜明的“自传性”笔调(即便套上第三人称的虚拟外衣,骨子里依旧透着“我”说话的声音)来写香港。先看她写于2013年的《到香港去》:内地妇女张英为了给孩子买安全的奶粉,积攒假期,只身跟了旅游团赴港,整篇小说借用的就是张英的“游客”视角,周洁茹让这位第一次到香港的女人跟着旅行团游历香港:港铁、金铺、星光大道、药店等构成了香港的都市符号景观。在这篇小说中,张英从“渴望”去香港,到最后“不想”去香港——“张英忽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来。”她经历的是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的隔膜和冲突。周洁茹用第三人称呈现一个陌生化的,“游客视角”下的香港,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其间还有夹杂着张英与内地游客的微妙关系:旅行结束过关时,张英被拦了下来,因为没人告诉她,每人只能携两罐奶粉出境,而张英买了四罐。这篇小说写得克制,没有故作姿态的批判和申诉。张英成了无数内地游客的缩影,她是短暂徘徊于港地的一缕幽魂。“到香港去”作为述行词已经构成香港小说诡异的地理空间符号。
再看《邻居》,故事发生在新界的公寓楼里。小说由“我”的梦境写起,叙说“我”邻居一对夫妻的故事。但其叙述笔调始终是隔阂和冷漠的。“我”经常听见女人高声尖叫,饱受干扰的“我”叫来保安查看,直到他们搬家,“我”也只与这对夫妇打过几次照面;小说的另一面,是“我”的朋友格蕾丝和她邻居的故事。在“我”的邻居搬走,新邻居还未入住的间隙,格蕾丝家对面屋苑有对中年夫妇吸嗅乙醚死于家中。《新界》写得鬼魅丛生,“不确定叙事”的手法颇有意味:对面屋苑夫妇的死,是“我”的邻居夫妻的某种“对位”。《新界》故意混淆真假:是否自杀的夫妇,就是这对神秘的、矛盾滋生的夫妇的另一种结局?周洁茹的第一人称令读者感同身受的同时又拉开了距离,这是叙述的奇妙之处,看似弥合,实则裂隙已生。这是陌生城市的“陌生化视角”。在这里,女性居住的房子,以及陌生的“邻居”关系,成了一个地理空间和精神性场所,它是符号也是指涉对象——周洁茹用房子这件“容器”来盛放女性个体经验和香港这座“孤岛”间的复杂关系。叙述者“我”带着“窥视”的姿势,勾勒出现代社会的“邻居”群体:他们一直在,又一直不在,他们始终是陌生人。
在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中,《旺角》显得很独特,作者用第三人称讲述“她”与一个香港警察的“偷情”故事,浮世的男欢女爱被赋予了另类色调。与警察分手后,“她”又格外想念他。在警察执勤的旺角一带他们相遇了,“她扭头望去,只看见他的背,他真是不能与她相认,偷情的男女,旺角的街头,陌生人一样的错过。”从私人的居住空间(《邻居》)到公共场所(《旺角》),旺角提供给读者的不单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还带有隐喻和指向性,《旺角》中的“她”,无意间闯入香港居民的“占中”运动(西方媒体称为“雨伞革命”),而至始自终,“她”对警察、街头帐篷、静坐者(躲在帐篷里吃面的人)所构成的强有力的政治景观都是陌生的:小说出现“她不明白”,第一次是“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第二次是,“她不明白她为什么在这里”。前者的“他们”指的是维持秩序的警察,第二个“她”,当然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了。换言之,小说写的虽是男女情事,一旦放置于政治运动、公民抗议的背景中,其反讽的意味就出来了,游离的、漠然的女主人公,对香港的社会政治景观的感受,与《到香港去》的“游客视角”异曲同工。
《尖东以东》,讲的是“我”的朋友周猫猫和他丈夫来香港旅游,“我”带他们逛街的故事。叙述者“我”退居故事角落,勾勒的出八零后周猫猫与九零后老公的婚姻悲剧。八零后的周猫猫是爱猫人士和环保主义者,相比之下,她老公却喜欢和他的富二代朋友混在一起,思想幼稚、不思进取,是个不折不扣的拜物教信徒,小说的结尾,“我”不无讽刺地回忆道:“周猫猫的老公戴着那块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值多少钱的手表,对我说,我要做团委书记。我终于笑了出来。”他们的“离婚”是必然,背后掩藏着价值体系的崩裂。周猫猫的拜物教丈夫,其实是无数中国大陆的“土豪”和“暴发户”的缩影,他们只关心名表的真假、限量版球鞋的希贵,他们对香港的认知还停留在购物天堂、资本主义社会的浅陋层面,对这座城市发生的政治气候的演变漠不关心,他们的精神早已被消费主义侵蚀一空。
以上四则“香港故事”,两篇使用第三人称(《到香港去》《旺角》),两篇第一人称(《邻居》《尖东以东》),然而它们内在的精神指向是相通的,它们描摹出在港的“我”与来港的“她/他们”的众生相,来港的“他者”与在港的“我”互为镜像,映照出陌生化视角下独特的香港社会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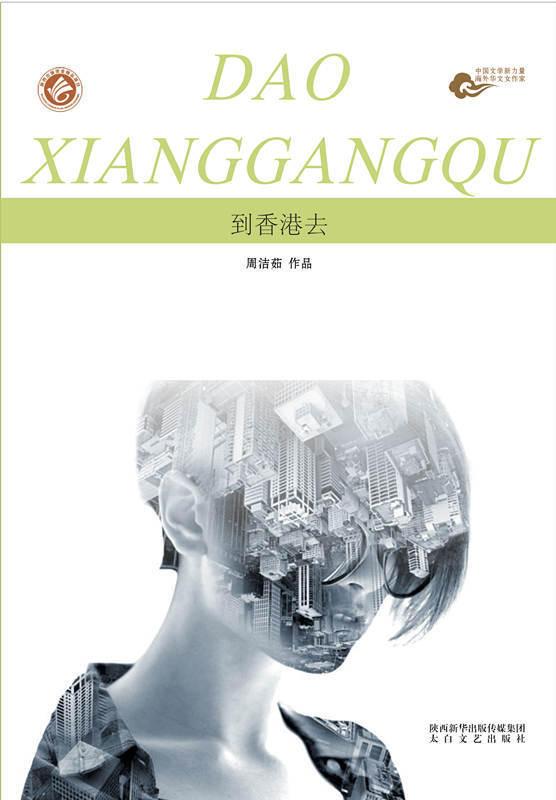
二.女性故事:经验“在场”与话语“缺席”
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婚姻悲剧,到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再到鲁迅笔下《娜拉走后怎样?》,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女性的地位问题、女性与男权社会及父权制的角逐较量一直是作家书写的重心。周洁茹也不例外,她的四则短篇小说(《结婚》《离婚》《幸福》《生病》)写的都是女性的生存疼痛和生命体验。这批小说聚焦女性经验的在场和话语的缺席,散发着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
这批小说单就题目而言是颇值得玩味的,“结婚”与“离婚”对应,“幸福”与“生病”对应。先看《结婚》,小说篇幅不长,类似“场景速写”,其主要场景只有一个:“婚礼”,而且是非常特殊的婚礼。“我”的朋友张英要结婚了,可“我”却直到婚礼前一小时才被告知婚礼改了地点。直到我“我”赶赴现场才一层一层剥开故事的迷雾。原来张英结婚,男方是再婚。婚礼现场,男方的前妻带着儿女来闹场,闹到最后警察也来了,婚礼没有办成。小说的结尾是一出荒唐的闹剧:大家围坐一桌,无力地“吃饭”;而在《离婚》中,周洁茹讲述的是“我”与三个闺蜜:米亚、飘飘、小奇各自的婚姻故事。小说开篇写四个闺蜜到寺庙里找和尚算命,最后四个人的婚姻都应了和尚的话,一个个落得离婚的结局。这篇写的是现代人的离婚群像。四个女人经历结婚、出轨、离婚、移民,被叙述者“我”轻描淡写,又透着疼痛。周洁茹把女性在婚姻中的离散、聚合、精神疼痛全写出来了,那么深刻而又到位。
再看另外一组小说:《幸福》和《生病》。《幸福》的讲述者还是第一人称的“我“,小说主角是小“我”四岁的侄女毛毛,主要情节是毛毛与两个男人(青梅竹马的富二代魏斌和乡下青年景鹏)的恋爱故事。魏斌对毛毛百般呵护,毛毛却不爱他,她夹在两个男人之间,后来毛毛意外怀了孩子,打胎过程得了腹腔炎,医院诊断她今后有生育困难。故事发生的场景大多集中在医院,这点与《生病》有着内在关联。《幸福》以反讽手法,聚焦女性的身体、权力、价值依附的问题。女主角毛毛是一个没有自理能力又对金钱没有概念的女人,她是《尖东以东》里拜物教信徒的翻版,毛毛租的房子堆满名牌包包和奢侈品,她的身体成了生育和维系幸福的工具。《幸福》中的毛毛被剥夺了话语权,她既没有很好的学历又缺乏谋生能力,与景鹏也没有共同语言。小说借“我”之口道出毛毛恋爱的悲剧,毛毛和景鹏唯一的共同语言在床上;而《生病》的女主角珍珠像极了另一版本的毛毛。“珍珠说,我的血永远凝固不起来的,所以我不能生小孩的。”珍珠遭德籍华裔男友的嫌弃,恋爱告吹,因为生病住进医院,叙述者“我”去医院陪护,由此展开叙述。《生病》由片段组成,没有具体的情节,写法上与《结婚》异曲同工。
从叙事方式上来看,四篇小说都采用第一人称,讲的是“闺蜜”之间的故事。叙述者“我”承担了讲述故事的功能:“我”既在内,又在外,既疏离,又融合。从小说整体的批判维度和审美内涵来说,它们是女性经验的集体呈现,从头到尾,女性的伤痛、离散、创伤记忆等经验是“在场”的,但吊诡之处在于,这些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话语场域中始终居于边缘,她们看似发声实则沉默。或许与作者在刻画男性形象上的模糊处理有关。他们的身份,有的是富二代、有的是到大城市奋斗的乡下青年,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授,无论地位身份还是价值体系,都与周洁茹笔下这些受伤的女子迥异。男性形象的模糊描写也是某种“缺席”,他们与女性经验的“在场”构成互补。在女性“失声”的地方,父权制社会的男权话语体系反而凌驾其上。
三. 异与同:小说叙事的双重奏
在香港故事中,周洁茹将故事的发生场所安排在香港的不同地理空间,并且苦心孤诣地以香港地名作为小说题目,这批小说处理的经验惊人的相似:女性个体的生存空间与香港这座“孤岛”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这点上,周洁茹的“香港股市”存在鲜明的“同构性”,用许子东的话来说,它们呈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一以贯之的“失城意识”,许子东称之为“此地他乡”,即身在此,意在彼,小说人物的归属感始终是游离的;而在另一条创作轨迹上,周洁茹勾勒出婚姻爱情中处于“爱与痛的边缘”的系列女性形象,她书写女性的经验和伤痛记忆。这批小说的空间地理通常是模糊的,只作为背景呈现。读者读到的都是现代都市的“速写”印象:咖啡馆、电影院(《离婚》)、医院(《幸福》)……此外较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异国”形象,《离婚》中的女人,总是(想)嫁去异国他乡:加拿大、美国……异国他乡在这里只是作为表层的空间地理符号而存在,就其深层结构来看,它们也构成了女性“逃离”伤痛记忆,试图开始新生活的精神空间(或许可以理解为这与周洁茹曾经的海外生活相关,它们共同构成周洁茹小说另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这点容易令人联想到爱丽丝·门罗那些书写女性“逃离”的小说。然而周洁茹始终站在“此岸”冷静克制地观望“彼岸”。小说《离婚》中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去到国外嫁给外国人而获得幸福。周洁茹笔下的“她们”一直处在分裂焦虑的精神状态下。
行笔至此,可以看到周洁茹的两条创作轨迹在涉及到女性生存经验、价值认同、道德伦理等维度上重叠并交汇。香港故事充满女性经验,女性故事包含香港经验,二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此基础上勘察周洁茹小说的叙事风格和审美旨趣或许更有意义。
周洁茹擅长在行文中用简练的甚至跳跃的语调讲故事,她不动用大篇幅的笔墨来细描,涉及到小说中“场景”的部分,都是一笔带过,从来不花费巨大篇幅进行繁复细致的描绘。那么,是什么构成了她小说叙述的主体部分?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1)利用人物对话推进情节。这或许是当代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叙事的一大特色,试看美国作家海明威和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前者有“冰山理论”,后者被冠以“极简主义”的美誉,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简练流畅的人物对白,某种程度上接近剧本的形式。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也好,女性系列也罢,人物的对话显得流畅、细腻,游刃有余,这批小说写出了独属于“闺蜜”的语言风格;(2)人物心理的带入带出,就像电影画面的淡入淡出,周洁茹将人物心理情绪的涌动通过间接引语直接附着于文本中,读者有时分不清这些言论究竟是虚构人物的,还是作者自己的。考虑到作者的女性地位,如此疑虑又显多余了。我们可以假定,周洁茹笔下女性的心声便是作者的心声,她们的伤痛与愤怒、孤独与绝望,是现代社女性心理情感的同位语;(3)第一人称叙事的频繁使用。周洁茹小说的谱系中随处可见作者的“自传性”乃至叙事声音的介入,可以说“我”的影子在文本中无处不在。即便在贯穿第三人称叙事的《到香港去》和《旺角》,第一人称叙事也成了潜在的结构。这点与周洁茹的香港/美国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认为它们只是作者生活的切片,它们被放置在小说这一显微镜下,成了标本。透过小说的放大作用,能清晰地看见其纹路、肌尖理和组织构造——它的病灶、癌变乃至死亡征兆,其实都无比清晰地映照出当代社会中女性个体生存的隐忧。
这是周洁茹小说叙事的双重奏: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水乳交融,彼此依存。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洁茹接下来还会继续写她的“中国故事”和“美国故事”,这三者会构成她写作疆域重要的版图。周洁茹的短篇小说大体采纳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没有实验和后现代主义,她的小说也不需要取巧于形式的先锋。周洁茹的小说介于通俗与严肃之间,在观照世相与描绘情事之间游刃有余。换言之,我们无需为周洁茹贴上任何标签,她笔下的人物活得如此立体,当代社会的隐约变迁,新媒体(QQ、微信等)的使用,在她的虚构世界中并置着,丝毫不显突兀。许多当代小说家写作上的缺陷在于,他们总是刻意在文本中彰显自身的创作意图,努力贴近时代,野心太大,格局太小;相反,周洁茹看似无意去经营宏大叙事,也无意于表征时代,但往往无心插柳,将时代和社会的幽微处揭露出来,如是,双声部汇聚成单声部,双重奏也是多重奏。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