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下午,专程从上海赶来的金宇澄和向来深居简出的阿城相聚北京言几又书店,共同探讨金宇澄最新出版的作品《回望》。《回望》可以看作金宇澄的私人回忆录,关于父亲和母亲,关于记忆与印象,当然也关于旧日的上海。

活动现场。金宇澄(中)与阿城(右)对谈。
中国式的叙事给人一种碎片化的体验
金宇澄表示,《回望》和《繁花》在创作过程上有很大的区别。《繁花》其实是一个和网友持续互动而来的产物,而《回望》的写作则是断断续续的。最早的一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算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在家听父母谈起往事的拼凑所得。接下来便是在父亲过世之后,慢慢收集关于父亲生前的材料,渐渐加深了对父亲的了解。金宇澄说,材料中其中几封信给自己触动很深,这些也都收录在书中。因此总体来看,《回望》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开始是一个引子,中间一部分重新审视了大量的史料,而最后一部分则由金宇澄母亲的口述组成。
这种近乎片段式的描写方式,其实和金宇澄的阅读密切相关。金宇澄说自己特别喜欢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喜欢看笔记体的故事。虽然西方的叙事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规模地影响了中国的读者和作者,但金宇澄仍对中国式的写法很感兴趣。“中国式的写法不是要把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而是就几句话,这总是给读者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体验,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
在谈及历史时,金宇澄也说自己不喜欢看头头是道、逻辑性非常强的大历史,反而倾心于类似八卦的故事,因为“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在眼前”。金宇澄提到清代李伯元所著的《南亭笔记》,里面记录了很多无甚由头的怪人。
比如晚清时代有个将军级的人物,是湖南人,常穿白色战袍骑白马,经常被认为是清代赵云。此人有很多老婆,但当他有了一大笔钱的时候就到上海玩。当时全国只有上海最好玩,因为上海有租借,有红灯区。他到上海就化装成一个乞丐,跪在有妓院的四马路上,手里拿着一沓手纸,看见一个女孩子就递一张手纸给她,一般情况下他会被骂被拒绝,但是也有心地很好的女孩带走了手纸。此人跪在地上把手纸发完就走了。把手纸带回家的女孩子发现手纸里夹着一张黄金的叶子。
金宇澄评价说:“这个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你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这么做。就好像在饭店里刚吃到一个很好的菜,就没有了,所以味道特别浓。这种小小的短章能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在《回望》里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小的细节。越是没有原因的短的叙事,反而能产生非常强烈的想象的空间。有些非虚构的写法是非常仔细地梳理一个人物,大致平衡和完整,甚至也有虚构的成分。但我想做的是只要觉得有趣的,就把它记下来,甚至于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和一般的非虚构不太一样。”
阿城则说在读《繁花》和《回望》时,发现两本书中都有一个上海地图,如果相互比对着看,会发现两张地图里的地点基本没有重合。假如金宇澄继续这样写下去,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密集的上海地图,每一个点都有自己精彩的、能够被读者记住的故事。而慢慢地,如果其他作者也加入,那么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上的串联将会非常丰富,读者会因此对上海这个城市有越来越清晰和深入的了解。“这是我从金老师的作品里得到的比较深的见解,我特别期盼他在以后的著作中能够把这个地图呈现得更加细致。就像以前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把整个巴黎和与巴黎有关的外省描绘出来,提供了一个最详细的法国地图。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地图,但现在看来,北京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开始建立。”阿城说。
中国的写实主义像气球,能拴住气球的点在于自然主义
《回望》开篇的第一句,是关于物件的描写。“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角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与此类似的细节,在《繁花》中也多,细细密密像针脚,铺排开来。阿城对这样的细节描写颇为推崇,阿城谈到十八世纪五六十年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他们开始对很多事情发生兴趣,希望对很多的点深入挖掘,这个挖掘导致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省,导致人们发现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是妖魔化的。
“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推力的结构和原来的环境渐渐就像一个岛慢慢升起来,露出水面,水都流走了,我们看到了遗址。这个岛对于影响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深刻地反省,这个反省导致对于革命的反省,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就有了新的详实的资料以供讨论和鉴定。这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波旁王朝的认识和以前也不同了。所以细节挖掘做的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会产生更普遍更深入的认识。”阿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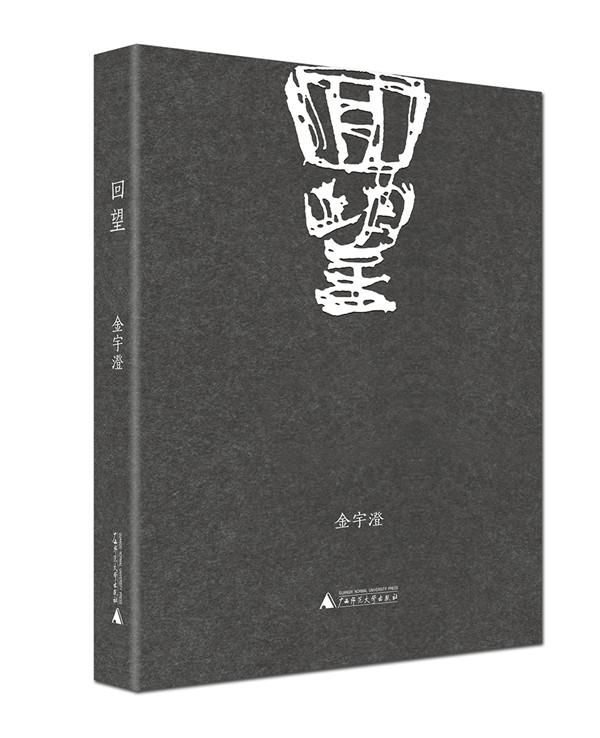
《回望》封面
阿城也由此谈开,讲到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一直在强调写实主义,但写实主义的基础其实是自然主义。像巴尔扎克、福楼拜这样的作家的描写,自然主义代表人物左拉认为,他们没有到达写实的极限,一定要通过自然主义达到写实的极限。到了极限之后退回来才能知道对于写实主义的把握是否有分寸、够分量。阿城说:“没有对这个底线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不好把握,看不清自己的写作在一个什么恰当的合适的写实的度。我在‘文革’时候看到了人生的绝境,就是底线,再往前走就是死亡。谁是乐观主义?当然是我,因为只要我一回头,就是亮。前面是最黑,我越偏头会越来越亮,越来越光明。在文学上这个底线就是自然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只要你一偏头,所有细节的显现、细节的意义在哪里等问题就会越来越清晰。”
阿城也谈到中国对于自然主义的态度一直以来是批判的,因为中国的写实主义是关于觉悟够不够的判断,是在讨论对于现实的认识。自然主义恰恰相反,里面不涉及什么价值判断,但却很有力量。阿城做了一个比喻:“写实主义一直像个气球,飘忽不定,必然有一股强风来,主流来,就随着主流飘,没有一个线能拴住这个气球,气球就是写作。气球的扣在哪,下面的点在哪?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
“张爱玲对《红楼梦》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它还是传递了一个价值观,比如后来贾宝玉出家了,那是很强力的价值观。但是《金瓶梅》不是,你看到的是自然生物体如何慢慢烂掉、死亡,本能的东西在那里来回蠕动。中国实际上是有比左拉在时间和空间都要早的自然主义传统的,其实有很多人继承了中国的自然主义传统,但没有人敢于通篇继承,而是局部继承。我看《繁花》很兴奋的一个点是,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这个补课的结果是非常正面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是对人最本性的反映,是敢于直视。敢直视它实际上就是直视自己。当人在自然主义的底线游走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看自己。”阿城说。

评弹版《繁花》。摄影:虞凯伊
金宇澄则顺着阿城的话延伸开去,从评弹改编《繁花》的尝试探讨价值判断的问题。《繁花》一书其实是评话的形式,是从头到尾一个人说话,变成评弹怕一个人说太累,就把它做成三四个男女弹弹唱唱。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判断人物的传统,分辨好人坏人的问题。“比如第一场就是繁花引子里抓奸的一段。评弹演员处理这一段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价值判断,最后也改成一个人做了坏事情所以是活该。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因为小说里的分析虽然是一个世俗的画面,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也不能说婚外恋的人就是坏人。评弹的人说这是师傅教的,首先要分析一个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叫开相。我们现在的观念在和传统亲密接触以后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也就是这些传统戏剧如果观念不改变,可能就不大有人能接受,因为它把东西简单化了。人的复杂性应该是我们要关注的,并让我产生了对于过去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包括对上海。”金宇澄说。
方言是泥土里自生自灭的味道
《繁花》一书因为采用了很多改良后的上海方言,因此引起了对于方言写作的热烈讨论,而在《回望》中,金宇澄没有延续方言写作。金宇澄表示当初用改良上海话的原因和自己多年的编辑身份有关。“因为我自己是编辑。有些方言的稿子,离开一个地方读者就看不懂,所以习惯让作者改一下。 等到我自己用上海话写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我自己可不能写让别人看不懂的上海话,就叫做改良。”
阿城则说读《繁花》时并没有阅读障碍。阿城认为接受教育的思维让人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步一步扎实,搞明白了才继续。但阅读恰恰相反,是个不求甚解的过程,即使现在全部读懂了,到了另一个人生阶段还会重读。因此不求甚解其实是阅读的常态,里面的方言读多了之后,可以结合上下文语境猜出来,并不会造成阅读障碍。阿城认为唯一损失的是一种方言的音韵之美,以及里面所蕴含的自然的情绪。
金宇澄则觉得方言是一个泥土里长出来的语言,它没有办法进入字典,因为每天都在变。所以当我们用方言写作,记录下来的就是方言在某个时刻的样子。“比如《金瓶梅》里的这种语言,可以看到当时有些话是那么说,但现在不说了。方言是自然的、泥土里的自生自灭的味道,是很有意思的。”

讲座现场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