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已经习惯有问题找警察,有纠纷找法官时,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乡村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如何维系?“乡绅”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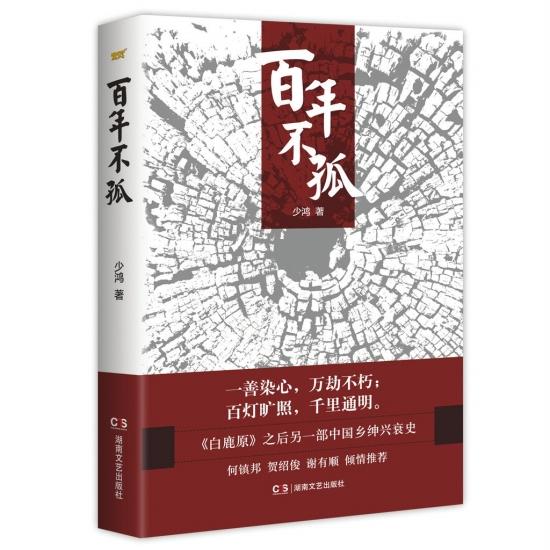

陶少鸿
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陶少鸿,进城已有几十年,然而他的笔下写得更多的却是乡村。虽然当过工人、进过大学、做过机关干部,但他说,“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因为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
如果说他七年前写的《大地芬芳》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那么新作《百年不孤》探讨的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乡绅命运的长篇小说,跨度百年,在他看来,“乡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曾经是乡村伦理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学长廊里,乡绅的身影被遮蔽。陶少鸿想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
乡绅不是官,却是基层治理的主角
“土豪劣绅”,这是今天人们“熟悉”的“乡绅”。
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乡绅”者,乃“在乡缙绅”之谓。“缙绅”字典里的解释指的是古代有官职或者做过官的人。由此可知,乡绅与“官”有着密切联系。
明清时期的乡绅由这样一群人组成:致仕、卸任甚至被罢免的回乡官员,以及现任官员在家乡的亲戚子弟;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监生,以及在乡试、会试中及第的举人和进士。
“这两类人虽然与现任官员不同,但前者是曾经做过官的人,后者则是将要做官的人(进士大多例外)。”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徐继存说。
他们不是官,却是基层治理的主角。他们处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
《百年不孤》塑造的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典型的乡绅,前者是晚清秀才,写得一手好字,讲究礼性,乐善好施。后者岑国仁曾给县长当秘书,见不惯杀人逃了回来,算得上是回乡的“官”。
在《百年不孤》描写的双龙镇有这样的习俗,无论是分家、不动产买卖还是邻里纠纷,都得有中人来做评判与见证,也得由中人来调解。
中人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人担当,才让人信服。而在双龙镇,最权威的中人非岑励畬莫属。李家两个儿子分家,房子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相争不让,就请岑励畬做中人调解了断。
陶少鸿笔触细腻,许多细节故事如同真实发生过。“实际上,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有原型的,是从我外公的家族故事生发而来,某些事件也的确真实发生过。”他说。
在“皇权止于县政”的时代,“村子里没有行政机构,没有法官、法庭,就靠乡绅来维护乡村的秩序。”陶少鸿说。
撰写《乡土中国》的费孝通对此有专门论述:“在政府的传统体系内,中央权力的触觉停滞在县里。每个县通常是由村民在地方上组织起来的一系列村庄所组成的。地方组织有着共同的财产,管理共同的事务,如宗教仪式和浇灌。这种组织的当事人不是由所有家庭里的代表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村庄里受尊敬的长者决定的。受尊敬的长者是那些有土地和身份的人,即那些和官方以及镇上绅士有联系的人。”
大多数乡绅顾及一方声望和名誉
乡绅里有没有“劣绅”?当然有。
但徐继存认为,“尽管乡绅贤愚优劣,固有不齐,但由于乡绅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使命,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
《百年不孤》中,为了减少溺女婴的恶习,主人公岑国仁索性成立了育婴会,“凡家庭贫困的人家,生女孩就资助一旦谷养育粮”。遇到灾荒年份,岑家开义仓救济。遇到河流拦路,岑家祖辈带头捐资修建风雨桥。
“其实,这些事都真实发生过。”陶少鸿说。“至今,湖南安化有一座永锡桥,是安化有名的旅游景点,就是我外公的祖父联合一些乡绅修建的,桥头至今还立着功德碑,写着他们的名字。”
“乡绅们做善事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我问他。
陶少鸿认为与文化传承和文化环境有关。“做善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好的名望,会引来村民的尊崇。”
“面子”是《百年不孤》中隐约提到的另一个原因,主人公乡绅岑国仁开仓放粮,重建义仓,村里人嚼舌头,“他是想要个吾之公那样的好名声吧。”
费正清说。“‘面子’是个社会性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
因此,乡绅大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份和行为,顾及自己的声望和名誉,讲究“面子”。
“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严重违反这些道理,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乡绅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
而乡绅的行为,反过来又可成为乡民的表率和法则。正如江西巡抚沈葆桢所写的《居官圭臬》所云“大凡一方有一个乡绅,便为那一方的表范。乡绅家好刻薄,那一方都学得刻薄;乡绅家好势利,那一方都学得势利了。若还有一个乡绅俭朴淳笃、谦虚好礼、尊贤下士、凡事让人,那一方中,哪个不敬重他、仰慕他。”
“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
“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费孝通说。
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挥着仪式的进行,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坐在首席,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
对于大字不识的农民而言,文字是具有神秘性和权威性的。
《百年不孤》中,岑国仁捧着写废的字纸,走到路旁的一座六边形四层的宝塔旁,将字纸倒入其中,划一根洋火点燃。这座塔就是字纸塔,塔身上刻着“敬惜字纸”的字样。“这也并非杜撰,湖南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塔。”陶少鸿说。
读到这个细节,在《百年不孤》的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贺绍俊说,“原来,以前的人对文化如此尊崇。”
因此,陶少鸿对“乡绅”有一个定位,“乡村伦理的维护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然而,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乡绅开始陆续分化和衰微,有的弃乡入城,有的投资办厂,有的转向自由职业……
当上个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陶少鸿被下放到安化农村时,他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夜晚,若有手艺人经过,请求留宿,“村民们会无条件接待,不要报酬,还特意打两个荷包蛋。”村里会设置凉亭,凉亭里常驻一人,每天烧一大桶水,供来往的人饮用。过河会有义渡,免费将人渡过河。“这些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由当地人提供一两担谷的报酬给凉亭烧水的村民。”
“扶助乡民,这是‘贤者’应尽的责任”
当陶少鸿写出《百年不孤》时,《“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恰巧提出了“新乡贤文化”。
“乡绅和乡贤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和区别?”
“乡绅已然消失,乡贤也不是乡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乡村的优秀人物,都是乡村精神领袖,”陶少鸿说,“不同点在于乡贤没有历史附着在乡绅身上的封建的消极因素,反而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与道德精神,起到营造现代乡村文化与道德伦理的作用。”
1999年,韩少功回到曾经插队的汨罗建了一座小院子“梓园”。他掏5000元给村里修水渠。为了乡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向当地市委书记写信“讨”过钱;村子里为修路规划吵吵闹闹,村长请“韩爹”来说了几句话。如今,“韩爹”是八景最有“话份”的人。
2016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登载一篇评论《“新乡贤”新在哪儿》比较了新乡贤与乡绅的区别后提出,“无论怎样‘新’、怎么‘变’,‘乡贤’的责任义务没有变。”
“一个人‘贤’与否,关键看他对‘不中’‘不才’之人,是‘养’还是‘弃’;照顾贫弱、扶助乡民,这是‘贤者’应尽的责任。”
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写“好”比写“坏”更难。写“坏”写出一个坏处就可以,而写“好”必须“好”得逻辑清楚,没有破绽。
《百年不孤》中,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是“极善”,开仓放粮救济难民、设立育婴堂防止溺女婴,“当然,他们也会有摇摆和内心纠结的时刻,重要的是,他们最终选择了善举。”
陶少鸿说,“直面历史与人性,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为他们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点赞,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与初衷。”
对话
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
潇湘晨报:您说小说契机是自己写作的原动力与内驱力,只有它出现了,才会写小说,才能写小说,《百年不孤》这部小说的契机和触发点是什么?
陶少鸿: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岑励畬、岑国仁父子的原型就是我外公。岑国仁的儿子岑佩琪与我舅舅的经历一模一样,甚至后来在小说中揭发自己二叔的事也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就想写出几代人作为一个乡绅,创业奋斗、乐善好施的故事,是乡村文化领袖的最后见证,是一部集家族、创业、精神传承于一体的百年史。
潇湘晨报:因为主人公的原型是自己的家人,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美化?
陶少鸿:我自己觉得没有,我写他们的时候,不会有意拔高,如果拔高,塑造这个人物就失败了。原型就是提供我一个契机,给了我一个感悟。
潇湘晨报:您曾说《大地芬芳》这部小说是您最看重的小说。那么,现在《百年不孤》出版了,它在您心中是怎样的位置?
陶少鸿:《大地芬芳》是写我父辈的故事,也有一些原型。《百年不孤》写的是母系长辈的故事。前者讲述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关于人的生存;后一部小说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这两部可以互补,看出百年来南方大地的变化。我觉得无论现在时代怎么变,那种好的、善良的传统文化都会传承下来的,只有这个东西,使我们精神更加丰富。
潇湘晨报:您在乡村待了八年,但乡村并不是你居住最长的地方,为什么作品更多写的是乡村?
陶少鸿:精神联系还是乡村更牢固一些,毕竟是少年时候在乡下待了八年,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对我影响也是最大的。乡村生活于我来说,最大的获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了人与大自然最紧密的联系。站在泥香四溢的土地上,你可以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看到四季轮回变幻的色彩,你会感到你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就是它的一份子;置身乡村生活中,你必须亲手种植庄稼养活自己,并因此而体悟生活之艰难,生命之坚韧。总之一切体验都会让你感到人生既忧伤又美好。这其中就会有审美意识自然天成,它不知不觉地渗入到你的心灵中,进而影响到你后来的生活与写作。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却又是诗意的,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乡土题材吸引我的原因吧。我写过各种题材的小说,但很大一部分是写乡村生活的,其缘由不光是熟悉那里的世俗人情,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有种割不断的精神联系吧。故乡永远是你的精神胎盘,无论你走到何处,都有条看不见割不断的脐带与之相连。(文/赵颖慧)
[责任编辑:杨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