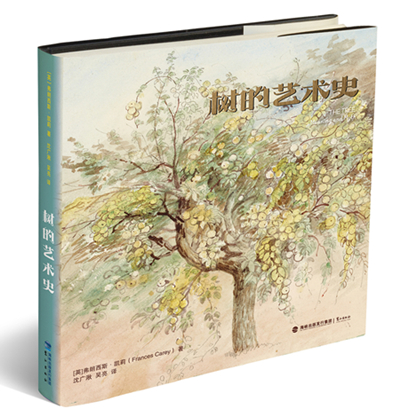
本文摘自在《树的艺术史》[英]弗朗西斯·凯莉(Frances Carey) 著 沈广湫 吴亮译 鹭江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万物都有一个历史,树也有它的历史。
树,在生物界只有“进化史”,在人类界则成就了一段“文明史”。
大英博物馆出版社新版的这本《树灵》,给读者们呈现出一部“树文明”简史!
树文明:树乃“人之树”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珍品和艺术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们手稿,藏品丰富、种类繁多。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竟还蕴含着一部关于树的“文明史”。多亏了此书作者弗朗西斯·卡莉这样的“有心人”的爬梳之功,使得这部简史被书写得如此趣味盎然。
树的进化不仅远远早于人类的进化,而且,人类祖先与树的紧密关联,也早于人类历史开启之时。树所构成的原始丛林,可以被看作类人猿的“家园”,也是早期人类的“子宫”。类人猿就是从树上爬下来进而直立行走的,站起来的人类祖先由此才获得了开阔高远的视野。2000 年10 月,最古老的人科女童化石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这块属于人类进化最早物种的南方古猿化石证明,人类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比原本预想的要晚得多,大约是330 万年前。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棵树木,也比任何单个的人都“长寿”得多。这棵老树是位于美国加州东部白山山脉的狐尾松,以近5000 岁高龄当之无愧地加冕为“树王”。在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老人家就已经三百岁了,“树王”与人类文明一起延续到了今天。
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之后,这个世界上的“树木架构”就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狩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使得人类开始砍伐树木以获得农耕之地,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候的全球变暖(酸雨随着大气而飘移)让树木年轮记载了人类气候的急遽改变,使得每棵树皆不可避免地被“人化”。这意味着,在树进化史的晚期,尽管树仍保持着自身的诸多自然属性。但已被人类“自然人化”了,或者说是被“文明化”。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 年)在《艺术的起源》(TheBeginnings of Art)当中就明确指出:“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即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过渡的象征”。早期人类开始把视角转向植物,创造包括树在内的植物装饰,其实就是将树纳入到了“人类文明体系”当中,树已经成为“人之树”!
在中西方之间:树的“神话”与“意义”
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所展示的就是人之树的“两个M”——“意义”(Meaning)与“神话”(Myth),毫无疑问,无论是树的意义还是树的神话,都是人类赋予树木的,而不是树木本身具有的,但先天属性与后天人化之间必然会形成相互匹配的关联。
原始人类可以通过树“通灵”,所以在人类早期史上有过大量的关于树的“神话”。如果读者都看过卡梅伦的电影《阿凡达》,就会对那棵巨大的“通神树”记忆犹新,Navi 族人通过自己的感受器(辫子)与神树相连后,借助神树的力量以获得启示与能量。这其实是对原始人类文明“树崇拜”情景再现,玛雅文明中的巨树就有这种“绝天通地”的巫术功能。
我曾在墨西哥游历,惊奇地发现,玛雅文化确实与华夏早期文明有太多近似之处,其思想核心是“巫的传统”,这与华夏文明同属天人相通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苏美尔文明与此后欧洲文明才是此岸与彼岸分离的“两个世界”的世界观。树在玛雅文明中就成为了沟通天人的“灵媒”,这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何共相似,该青铜神树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铜树上站着九只太阳神鸟。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历来重“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树在农耕文明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早在《诗经》当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句,诗句中的杨柳是中国人抒情达意的文学意象;孔子中有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处松柏的万古长青、苍劲挺拔、刚直不阿间接成为儒家道德的物化象征。
在中国古典文化当中,树的形象经常出现,也成了华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在元代山水画之后,画中树木常常以“一枯一荣”的面貌出现,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枯笔与润笔的比照,更是阴阳协调与互动之智慧的显现。在绘画、陶瓷、家具、文玩当中,树更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隐喻”,被赋予了以吉祥向善为主的民俗意义。当然,华夏民族的“实用性”
品格,也使得金钱榕成为“摇钱树”的代理者。更有趣的是,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差异,中西方对待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夏娃诱惑”的故事根深蒂固,夏娃由于在伊甸园被蛇诱惑而偷食了苹果树上的禁果,由次世人知道了“羞耻”,亚当夏娃获致了负罪感。美国人类学家贝内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 年)就此归纳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相形之下日本文化则由羞耻心所推动而成为“耻感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断然二分,如盎格鲁- 撒克逊的英格兰和多元文化混血的墨西哥,在基督化之后皆仍保存着耻感的社会大众心理。
当今中国思想家李泽厚则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照,中国文化乃有乐天派取向的“乐感文化”。但是,中国儒家的伦理传统仍要人“知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礼法来德化万物,百姓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松柏之类的“比德”手法,其实就是将高尚的道德与树木品性进行伦理类比,所求的乃是“善美交融”。
与中国的“伦理本位”传统不同,欧洲还有一个强大的“科学传统”,这就使得树木也
被纳入到近现代的植物学体系当中。《树灵》果然是西方学术普及的产物,它也从知识论的角度描述了树木的基础知识,在本书“树木馆”章节,更是将进入文明视野的树木形态进行了划分,就好似中药铺子里面的药匣子一般,将各种树条分缕析地进行逐一研究,这恰恰与中国那种模糊思维的传统形成了对峙之势。实际上,每个树种内部的文明都是相当错综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无论是广泛分布在北美、欧洲的桦树,还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的喜马拉雅雪松;无论是佛陀在菩提树下修得觉悟,还是象征永生的蟠桃树,皆形成了自身的“自然—文明史”,只要您耐心阅读,就会发现《树灵》如此书写的高妙之处!
“生态启示录”: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
人们总是说,我们来自自然,又复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现代文明阶段变得愈加紧张,《树灵》也促发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积极启示。
从人类的先祖到现代人类,皆与树产生了复杂而亲和的关联,树本身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明的存在。自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化”的伟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真正的荒野变得愈来愈少了。想一想黄石公园里面的树木经历了1988 年那场大火后,36% 过火面积使得许多树木都是新生的,已并不是上古荒野的原貌,而且许多动物物种也不是美洲大陆的土著动物了。再想一想,公园里、街道旁的树,从小在温室亦或室外栽培的时候,都已经被人工
培育了。为了适应公园抑或道路的“框架”,它们更是经常被进行人工的修剪与处理。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树的人工化”。这种人对树的培育方法,表达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审美观。如果你比较一下凡尔赛宫园林与中国苏州园林里面的树,你会惊奇地发现两类“树的人工化”手法,这两种手法各自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法国园林里面的树往往采取几何造型的手法,把树修剪成三角抑或半圆的形态,这种欧洲园林的“树之美”如果出现在中国园林里,一定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当今城市中被修剪整齐的树篱都是此种西化产物。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道法自然”,往往希望树木长得歪歪曲曲,很少有直线形的修剪,越是弯曲的树越被认为更符合自然形态。但有时不免过犹不及,为了达到这种自然形态,树苗从小就被盖上了“铁笼子”,以使得树木的枝干变得曲折生长,这其实是另一种人工化的手段。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看,这两类人工化都是人类对于树木自然生长权利的干预与剥夺。
所以说,如何在人工化如此强势的时代,重新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与生态关系,变得
相当艰难而又绝对必要。“生态文明”也要求人与树之间形成崭新的互动,还有什么比让树木一春一抽芽、一秋一落叶、一年一枯荣、一岁一年轮这些自然现象更美丽的呢?这也是
《树的艺术史》给我们读者的最高启示。由此,《树灵》可称之为一本“生态启示录”!
[责任编辑:杨永青]